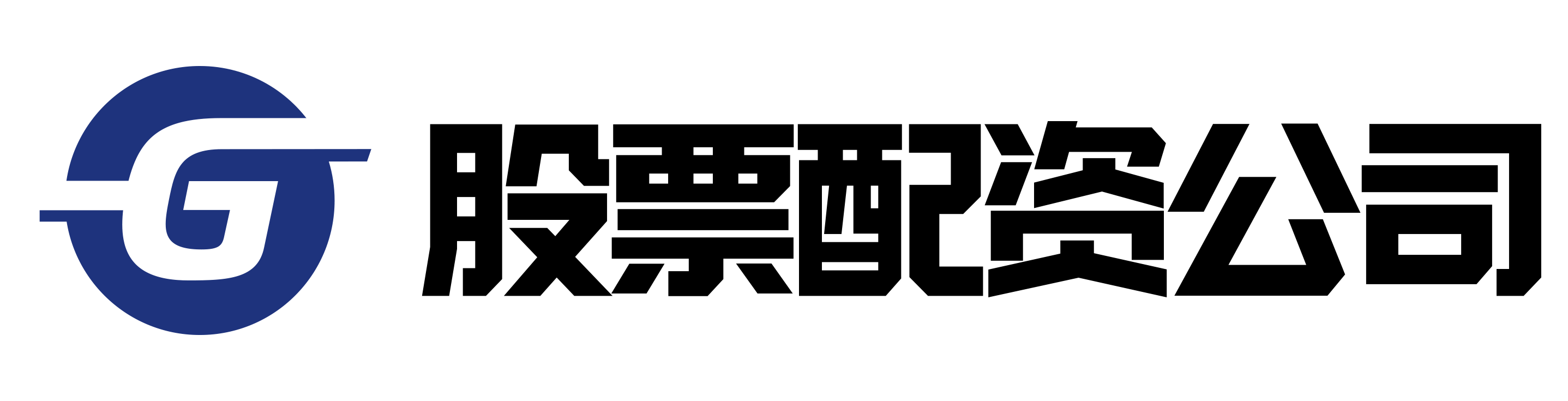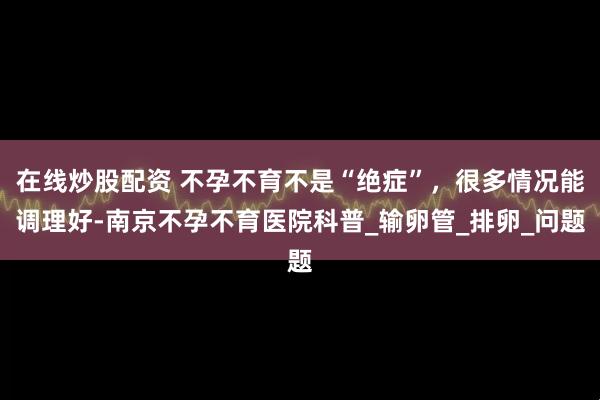在线炒股配资 他是中共一大代表,37岁被人密谋杀害,若能活到建国后地位不一般

“李先生,您的话里句句是火!”——1927年5月12日武昌中山大学灵堂前,一位学生抹着眼泪低声说。李汉俊微微颔首,转身面向挽联在线炒股配资,谁都没想到半年后那团火会突然熄灭。
李汉俊出生在1890年夏天的湖北团风县,家境谈不上殷实,却重视教育。村里老人常念叨:“那孩子七八岁就能通篇背左传。”稚子背经书固然罕见,更罕见的是他对“外面的世界”有着近乎执拗的好奇。1904年清廷选派官费生,他以一张几乎满分的卷子被录取。十四岁的少年第一次坐上海船,奔向日本横滨。

东京求学之初,他主攻土木工程。要是按常理发展,也许他之后会成为一名铁路总工程师。然而,1914年《共产党宣言》日文全译本悄然在学界流传,他读完后整整三晚未合眼。试想一下,一个工科生突然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,周围同学都觉得他“走火入魔”。更戏剧化的是,这种“走火”竟得到了教授赞许,教授在推荐信里写下“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”几个字,这么高的评价放到今天依旧分量十足。
1918年冬,他回到上海。那一年上海滩风头正热的是法租界影戏与租界咖啡,但他却钻进图书馆,把大部分时间耗在翻译和撰稿。不到一年,署名“汉俊”的文章频繁出现在《东方杂志》《民国日报》副刊,主题只有一个——马克思主义。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,当时的中文世界缺乏系统译本,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填补空白。有人统计过,中国第一批广为人知的马克思、恩格斯原著,他翻译的占了近三分之一。
1920年8月的上海厚福里,狭小弄堂里挤进几位青年:陈独秀、李书城、李达,还有李汉俊。他们商量成立“上海共产党组织”,并推举李汉俊起草《共产党章程》,这份译自俄语、融入中国语感的文件后来被视为我党最早的政治纲领。陈独秀南下广州后,上海的日常工作由李汉俊统筹,他口袋里常揣着上海到武汉的火车时刻表,因为隔三差五就要联络董必武等人在长江沿岸成立支部。那时候组织薄弱、经费紧张,他靠翻译稿费贴补差旅,字字都是血汗钱。

时间来到1921年夏天。中共一大原订在法租界柏林咖啡店楼上召开,却因租界巡捕暗访临时改址。那晚,法籍警官“无意”推门,正碰见会场。李汉俊懂法语,他笑着迎上去,寒暄两句后将对方请到窗边,让其俯瞰黄浦江夜景。短短几分钟,巡捕被花里胡哨的灯影吸引,自顾自离开。随后他果断决定转场嘉兴南湖,才有了那艘红船上的最后议程。多年后参会代表回忆,若非李汉俊的机智,会议极有可能流产。
人无完人,分歧也在成长。一大闭幕后,关于“是否立即组织公开工会”这一问题,李汉俊同陈独秀观点南辕北辙。情势所迫,他辞去上海职务,于1922年初赴武昌继续教学和宣传。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每周二下午,他在阶梯教室开设《资本论》选读,据说旁听学生常常把过道占得满满当当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对年轻人采取“头脑风暴”式互动,早已超过那个年代传统讲堂的范畴。

1925年至1927年工潮汹涌,湖北境内出现了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纱厂罢工。李汉俊白天讲课,深夜到工棚里与工人交流。他习惯夹着一支粉笔,在地上勾勒供求曲线,用最朴素的方式解释剥削。有人惊讶:“这位戴眼镜的先生竟然能把艰涩理论讲得像说书。”可惜火焰太耀眼,也更容易被盯上。1927年春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李汉俊被列入“首要危险分子”,6月在武昌江滩被捕,随后被秘密押往南京雨花台附近,37岁的生命就此定格。
关于他的遇害经过,史料说法不一。有研究者指出,他曾试图同看守辩论,甚至愿意再写一份自辩书,结果被特务以“半夜转移”名义直接枪杀。尸体被草草掩埋,家属直到事发两月后才通过流亡学生得知噩耗。那时的中国,哀悼烈士风险极高,一束白菊都可能成为罪证,于是他的事迹逐渐淡出公众视野。
新政权成立后,中央开始系统梳理早期革命者名单。1952年初,国务院办公厅寄出一封公文:确认李汉俊为革命烈士。紧随其后,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手把“革命烈士纪念证”递给其长女李月琳。现场气氛庄重而克制,年过花甲的李月琳泣不成声。许多与会老同志提起他,都会叹一句:“若李汉俊能活到今天,中央理论战线非他莫属。”

这种惋惜并非溢美。作为少数集翻译、组织、理论研究于一身的早期党员,他对欧洲左翼学说理解透彻,又能结合中国本土情况给出务实建议。更具象地说,要是他能参加建国后的政务院高教部,或许在高校马列教学体系上会大展拳脚;又或者,他会被调往中央编译局,为《列宁全集》做校订。这些假设如今只能停留在历史爱好者的想象,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那束过早熄灭的火种心存敬意。
武昌江滩的潮水日日涨落,雨花台的松柏一年比一年繁茂。大概只有翻开李汉俊的译稿、研读其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时,人们才能切身体会到什么叫“把青春写进纸页”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他把“自由平等”当成工程图纸上的坐标系,试图给旧中国找到最坚固的支点。如今读来依旧锋芒毕露,这就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益升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