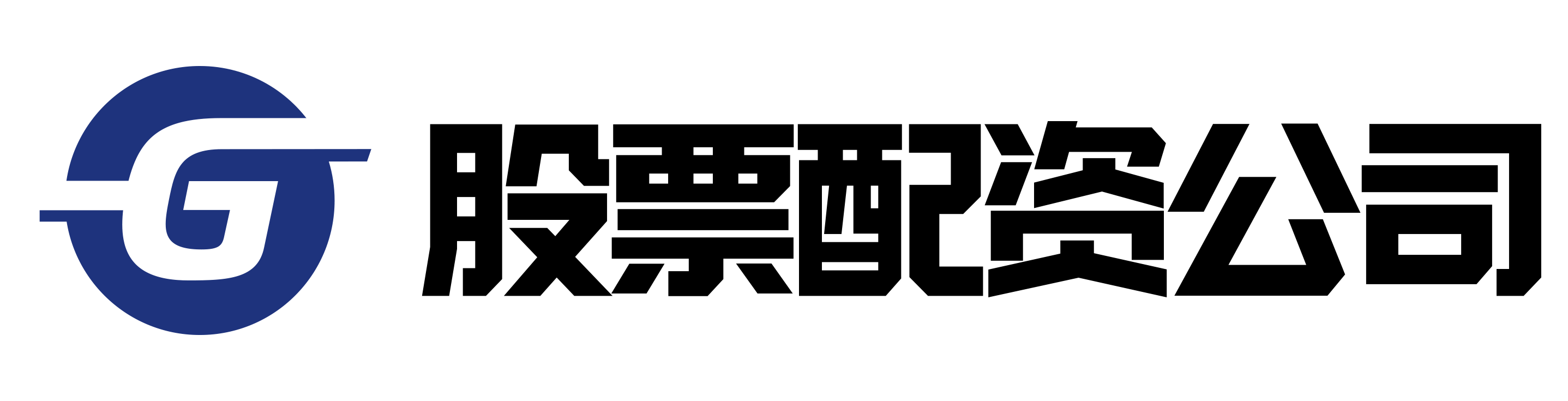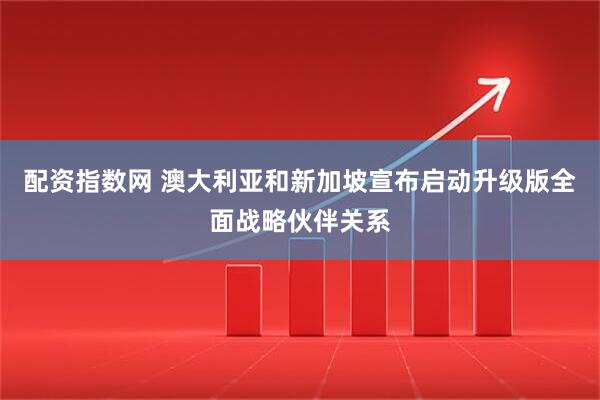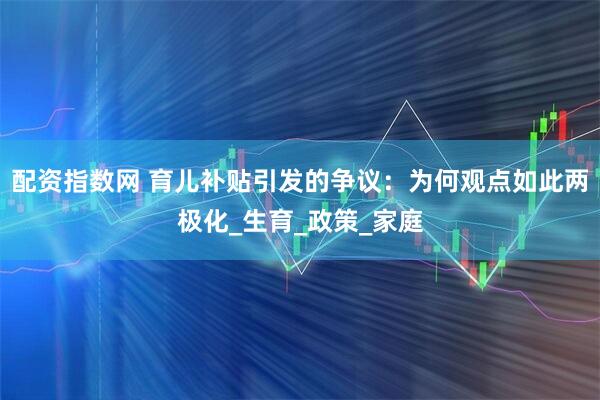配资指数网 81年,45岁的李敏病倒后独自住院,秦基伟听闻后:孔令华调来北京

【1981年3月配资指数网,北京协和医院】 “护士同志,别通知我丈夫。”李敏低声说。 “明白。”护士点头。
她想悄悄把这一场高烧扛过去,一如多年前扛住贫血、产褥热、甚至那几次大出血。对外,她是毛主席的女儿;对自己,她更愿做一个不麻烦别人的普通病号。
病床上的寂静,把她思绪拉回几十年前。1946年冬,北京西山的八一小学操场上,年仅11岁的李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诗,身后高她半头的帮着擦灰。那天风很冷,少年一句“别冻着手”让她记了一辈子。

进入中学,两人都成了班干部,会议、板报、春游,总在一起。1958年高考出榜,李敏拿到北师大的通知书,孔令华也被北航录取。爱情顺理成章,可第一道槛却横在孔家——将军坚决不同意:“我一个起义将领,哪配得上主席闺女。”
孔令华没退缩。他把情书塞进信封,字字铿锵:“不论身份,只论真心。”李敏在北京传染病院打点滴,听医生数脉搏的间隙,一笔一划写下回信。信送到中南海,毛主席听完女儿汇报,先问:“孩子家底摸清没有?”又摆摆手笑:“既是孔从洲的儿子,我放心。”
7月的丰泽园远没有想象中张灯结彩。主席亲点三桌家宴,四百元稿费,一只大红喜字贴在老式玻璃门上。临散席,他拍拍新郎肩膀:“丑媳总得见公婆,带娇娇回去拜见父母。”说完又朝贺子珍使个眼色,母女俩心照不宣。节俭,是这个家的老规矩。
婚后,李敏住进丰泽园西楼。毛主席忙完文件,总会敲开他们的小厨房,道一句:“饭熟没?留我一筷子。”日子平淡,却掺进了江青的醋意。1960年,为避嫌,两口子搬到中南海一角的平房里,自己点炉熬粥、洗尿布。

1962年10月,儿子降生。主席隔着半城风雪赶来探望,连声说:“今年我七十,又升一级。”取名时,他原想用诗经里的“宥”,偏被亲家提议“向列宁学习”。思索片刻,他写下“继宁”二字,笑称“既中国味,也寄托革命理想”。
孩子带来喜悦,也带来经济窘迫。供给制一视同仁,产妇加餐不在章程里。孔令华只得用旧煤油炉煎鸡蛋饼,给李敏补身。主席多次表示可从稿费里贴补,李敏却打报告谢绝,理由简单:“年轻人得自己过日子。”
紧张的日子刚越过去,浪潮又起。文化大革命爆发,李敏因“特殊家庭成员”屡遭审查,一度被隔离。身体不好,精神压力更大,她常说一句玩笑:“我比不上普通战士能吃苦。”可说完还是硬撑。
1978年后形势逐渐缓和,她调入国防科,搬进部队大院。丈夫在外埋头导弹型号试验,三口之家难得团聚。1981年初,她连续咳嗽、低烧,被检查出肺部炎症合并心律问题。怕耽误孔令华正在进行的某型防空导弹验收,她偷偷住院,只让儿子陪夜。
偏偏天不遂人愿。孔令华的战友探亲路过,认出病房里消瘦的李敏,一个电话打回部队。孔令华听完急得直抖:“病情怎么样?怎么没人告诉我?”晚上八点,他向领导请假,连夜坐上军车回京。

第二天清晨,李敏醒来,看见丈夫站在床边,眼圈通红。她苦笑一句:“这下瞒不住了。”短短对话,让病房空气都酸涩。
消息随后传到北京卫戍区司令秦基伟那里。秦老将军翻阅人事卷宗,放下茶杯对秘书说:“组织不能让老孔分身乏术,调!到京工作。”几天后,任命电报拍出:孔令华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。
调令到手那晚,孔令华握着电话向秦司令致谢。电话里传来河南口音的叮嘱:“主席对孩子们向来严,有事别硬扛,组织是靠山。”一句朴实,掷地有声。
职务调整后,夫妻俩终于稳定在首都,李敏身体逐步恢复,又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俄文资料,帮国防科室完善技术文献。她常自嘲:“我就是一块螺丝钉,别松就行。”老同学聚会,她从不谈当年荣光,只聊菜价、公交、孩子升学。

年岁渐长,李敏依旧保持晨练。南长街的垂柳下,她慢跑几圈,再掏出小本默背唐诗。偶遇路人认出她,她摆摆手:“别拍照,我跑得不够优美。”句式轻松,却写满一个将门之后自持与低调。
很多年后,有人问秦基伟当年为何出手相助,他呵呵一笑:“战友有难,能袖手吗?再说,是贺子珍把我带进红军队伍,我欠她一个情。”短短一句,历史的脉络与人情味尽在言外。
李敏把那份情记在心里,从不张扬,也从不遗忘。她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家人,也守护那段跌宕的岁月。
益升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